
「對話練習」是由大憨撰写的一份身边人「工作状态」的田野手记,这是朋友们的状态存档,是我个人状态存放的地方。观察到身边人工作方式的转变,期待自己能捕捉记录点什么来“肉身归档”。更重要是,把写作一份笔记作为连接朋友的一个途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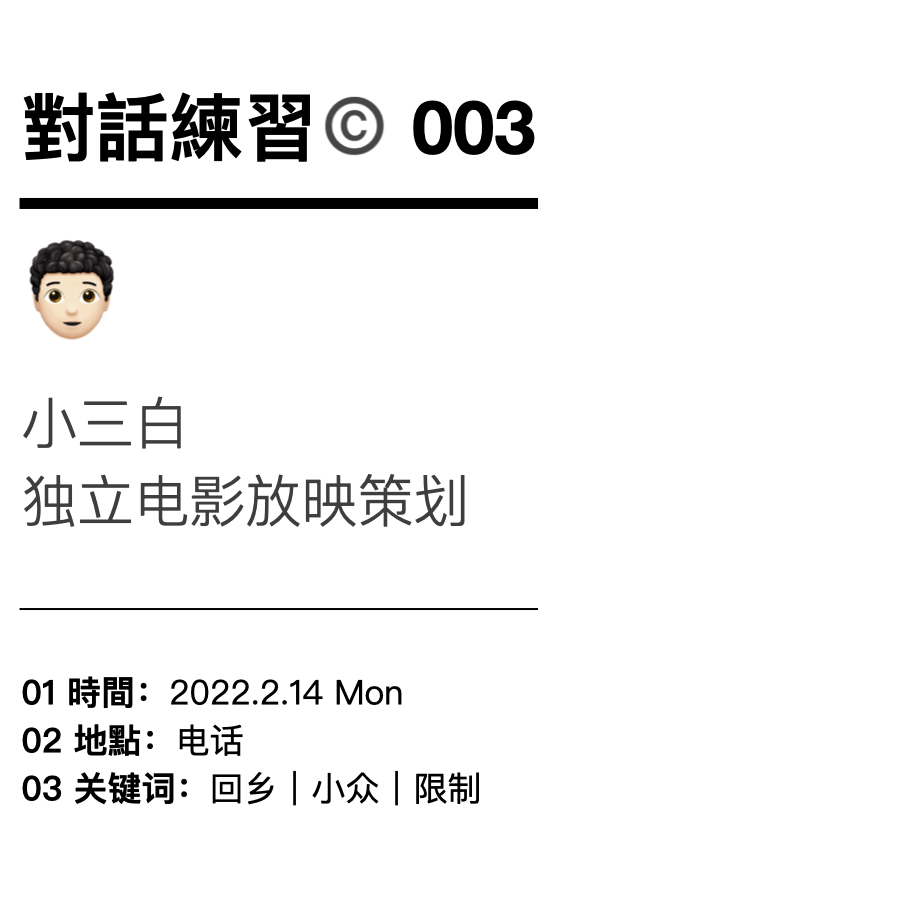
# 一个问题:如何处理身边现实的「限制」?
my quesiton
刚认识小三白时,是去北京一家独立电影放映机构看片。那时他们刚起步,每次放完片子总喜欢喊上志愿者、观众、有时再加上导演,一起去喝酒吃饭,几乎每周都会见面瞎聊,慢慢熟络起来,是我那个阶段的滋养之一。再后来,我回到深圳,失去联络。再和小三白联系时,她已经决定离京回家乡徐州自己做独立电影放映。
让我意外的是,小众放映在北京都是个不赚钱的生意,回到三四线城市更是小众。我当然好奇她为什么选择回乡,这个接受的过程是怎么发生的?我更好奇的是,35+以后,回到家乡,在四线城市做一份小众的电影放映工作,她如何理解环境的「限制」?如何处理工作和周围现实的关系?
# 一次对话:三十而「立」,找到立住的位置了吗?
raw material
可以接受啃老,
就可以回家了。
憨:回徐州考虑了很久吗?
白:也不完全是,我觉得最主要是心态问题,当你决定放下了,觉得啃老是可以接受的事情就可以回来了。对。
原先是肯定不愿意说「啃老」这个词跟自己有啥关系,肯定很难过,但是现在觉着这可能是一个阶段,时间也不会特别长,而且我也不可能是一分钱收入都没有。
憨:在北京离职了以后还继续待了一年。
白:对,徐州也是想了好久在想说要不要回来做点事。
最大的考虑我不用在北京租个房,你租个房其实也不是天天有什么事干,就是在那坐着,然后时不常的出去还出去的事都是花钱的。后来因为疫情我们也没有什么活。不如回来找一个不干也没有多少消耗,干了还能赚点钱就这种。
憨:回徐州做放映,环境的限制它是一个问题吗?
白:我是觉着是个问题,但也不是问题,因为徐州没有,所以你是第一个做这事儿的人,但困难肯定是有,而且困难比省会城市南京武汉要大得多。但做这几场发现还是有人有兴趣,就跟咖啡馆一样。前年回来发现徐州有很多咖啡店了,愿意点一杯咖啡坐一下午闲着没事的人,可能对电影还是有一些爱好。至少我是市区的,不是县区的,你知道我特别不想承认丰县是徐州的,很生气。对于电影来说,我觉得不管是在哪个城市,它都需要有这种不同的声音。
憨:你现在在做的是一个什么事情?
白:我现在做是为徐州观众推荐小众艺术电影、动画、纪录片等作品,因为徐州有这种小众需求的人很少,现在还是在培养观众,还很难做成策展系列,只能慢慢的先从影院小众包场开始。
我们叫「观察纪·观映团」,「观映」其实是观看和放映之间的一个桥梁,我想做的是一个交流的空间,是作者和观众之间交流的一个空间,所以我一定是会有映后的。即使不是导演的映后,也一定会有相关话题相关的人去讨论。
憨:相当于现在回徐州要先去做北京那种初级阶段的事情是吧?
白:还达不到,我们就只有民间放映,民间放映就是能把它放出来就好了,找到一拨人愿意看这些片的。在北京其实他已经有那个观众基础了,更期待你有作为策展机构的自我表达。
其实是第一场《东北虎》不太好,也因为卖不出去票,慢慢第二次第三次可能就稍微人会多一些。其实跟北京做放映是一样的,还是非常私域的那种流量,慢慢积累。
放到一个更长的历史里去看,
没有找到工作,
难道就不活了吗?
憨:你中间不工作gap过三四年,会不会有那种反思,比如说为什么很多人都可以找一份工作,自己不愿意去选那份工作,是不是太任性了?或者是说已有的环境里面,难道我就不能发挥我的主动性?
白:我现在不会这样子想了。
去香港之前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子想的,为什么别人都觉得挺好的,为啥我就在这干的那么费劲?这个问题就在于你认不认可这个环境,如果你是认为这个环境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你自己,你就一直在找我怎么改,但是你在改的过程当中,你觉得你自己更难受。后面我去香港以后,你会发现原来别的地方的人是那样生活,这种生活方式跟你在内地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就会回来思考说内地的环境是我的问题还是环境的问题?当你认为可能是环境有问题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必须要改我自己。
憨:我还是在想你能接受啃老,这个「接受」的过程是什么?
白:我不知道这个过程是什么,但是你把它往长远看,你真的有一两年或者几年没有工作,这是一个很少见的现象吗?,并不是。我说的不是那种真的瘫在家里的有那种想法了,而是像我们这种还想干点事的那种。比如老辈如果你被分为黑5类 [1] 就没有工作,但没有工作你就不活了吗?那不是一样还是有活路,还是能想招儿怎么活嘛。
憨:你刚才说过往比如说放在更长的时间里,不工作的人有很多吗?我都没有这个概念。
白:我觉着有,我觉得现在已经到了第二次唱「心若在,梦就在」的时候了,就是刘欢关于90年代下岗潮的那首。
寻着这个历史,我就觉得我们不是最早的那一批了已经。那个时候就是先上山下乡的所有人都没工作,然后都是分配,但是也有一部分就是不给你分配,因为你成分不好。所以那不就是没办法,黑5类就只能投机倒把,自己弄点货,然后赚差价,弄点小生意这样的。那比如现在大厂开始裁员,又到了这种第二批下岗的感觉。
我觉得在经济环境当中,我也不是那种很符合他们用工需求的那一拨人,所以我也有半被迫不工作的部分。
三十而立的「立」,
不是成家立业,
而是你能找到一个自己的位置。
白:我后来有一个变化,就是想「我想怎么活着?」就是把它想到一个更宏大的那个方向上:我是想就找一个坐班的工作,然后天天可能无所事事,其实你没干什么也很耗费精力的这种方式活着;还是说你有事做事,然后做完事有收入,没事的时候就闲着,干点自己的?那肯定是后者。当变成了你想怎么过这一生的命题里头,你就觉得好像也还行,现在的状态也还行。
憨:闲着你会难受吗?
白:闲着,并不是跟世界断绝关系的那种闲着。我觉得我可能在徐州想要做这件事情,做这个的事的话也是给自己找个事干,同样也是一个跟外界保持联系的一个方式。因为你要做这个的话,可能我之后会想要跑跑电影节什么的。
但是你必须得有一个身份,这个身份是要你做什么事。像一个朋友,他自己觉得自己是个影迷,但他现在已经被别人觉得是个影评人了。他一直在看完了片子一直会在豆瓣上写影评,所以他在影迷圈非常有名,他自己也不见得就接受这个词,只不过你得有一个相对的身份。
憨:你说的身份,像是他找了一个位置,一个身份。
白:这个位置也不见得是一个工作的位置,而是你自己对自己的一个位置,你以什么样的角色去跟其他人交流。即使说我就是一个驴友,我花钱去旅行的时候也是一个交流。但是这个问题在于你这个事情是不是有后续,你做的这个事儿是不是能连续做。我那个朋友不管别人叫不叫他影评人,他都会看完了写影评,他有一个能坚持做的事情,我觉得就有一个比较确定的位置去跟别人交流。
包括你看《侣行》那个节目北极求婚,南极结婚的,这个事本来就是他们业余的一个事儿,当把它变成了一个一直长期来干的事,它就变成了一个事儿,一个事业,或者说一个就慢慢能赚钱的一个事儿,这不就是他的一个位置?他这个位置最开始也是他自己给自己定的,也不是说我找了一个工作去定的。
憨:这个好棒,打通了我刚才想问的一个问题,你说想了很久要回来做点事,我就很想说这个「做点事」怎么界定它,跟工作区别是啥?感觉它其实可以归到位置或身份,是一个自己给自己找的。
白:对,我觉得是一个身份,就你怎么定义你自己,然后你怎么定义你自己跟世界交流的一个位置和身份,就是以什么样的身份跟世界交流。
憨:这个身份它是慢慢出现的,还是。
白:其实是慢慢出现的,或者说那天说三十而立,那个立其实我觉得是这个「立」,并不是说你要成家立业的立,而是你能找着一个你自己的位置和一个身份。
再说一个,当我们有了定位之后,其实我们可接受的工作就更宽泛了,比如说,我可以去咖啡馆做服务员 ,以前我不愿意做,但现在你的目标不一样了, 你不是通过它去实现自我的理想自我实现,而是为了赚钱。那就很简单了 这些事情都可以做。
从不分配到分配,到自由选择
中国急速的变化,
父母经验失效,也来不及接受
憨:我在想你可以选择现在这种生活方式,是不是还是因为你父母接受,回家以一种较低成本的方式去做,它能够变成你的一个安全感?
白:最开始我没有这个安全感,是因为家里不允许都是好强的,他会觉得你这样不对。但是现在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妈妈的态度其实是有改变的,她支持我啃老。
我觉得是因为父母那一辈也没有经历过这种大时代的变化,网络就把之前的逻辑推翻了,而且中国这几十年这种变化特别的大,它从一个80年代还分配,到不分配到这种你必须要自由选择,它是一个很急速催化的过程,父母也没有那一辈来说也没有那么快的一个接受的程度,他们可能接受不了,那他们的反应就是拒绝。他接受不了,但是新的他也不知道是啥样,完全是因为他没有经验。
实际上我们最早一辈一辈的过都是基于老辈的经验,然后有那么一些新的发展就已经算突破了,但是中国太快了,一下子转变的时候,他们也不知道该咋办了。
# 一份田野手记:从工作伦理到工艺伦理(ethic of workmanship)
field notes
跟小三白聊完天,我第一反应是去搜“心若在,梦就在”这首歌。
听刘欢唱那么多遍,我不知道它的历史背景居然是1998国企下岗潮。1998年国企改制,提高经营效率,国有固定工逐步转化为合同工,98年至20年间,几乎每年有900万工人“被人员优化”。下岗工人中很多在40岁到50岁之间,上有老、下有小,又很难学习新的社会技能。砸破“铁饭碗”后,从工厂到市场,一代工人的沉浮与迷茫。看黄灯写《我所亲历的90年代国企下岗》,心酸唏嘘。
搜了搜日本和韩国的同期的历史:
90年代末,韩国雇主寻找各种方式降低劳动成本,白领工人终生就业的长期传统难以为继,裁员的威胁对很多工人来说变成现实,韩国在1996年进行自朝鲜战争结束以来第一次全国性总罢工,以抵抗新劳动法在裁减工人、 雇佣临时工或替代罢工工人方面给予雇主更大的权力和灵活性。[2]随着2000年后韩国新增就业增长缓慢,“经济危机世代”遭遇了“求职冰川期”。年轻人失业率是整体失业率的两倍多,20~29岁人群中处于雇佣状态的不到50%。“新经济自由主义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是提高雇佣弹性,曾经拥有“终身雇佣”传统的韩国很快成为经合组织(OECD)国家中“非正规职”比例最高的国家。[3]日本在二十世纪八○年代初之前,高度家父长制的职场文化,让大部分上班族一辈子都会待在同一家公司。极高的就业安全性,让员工不敢踏出公司一步。但到了一九八○年代初期之后,白领上班族在日本劳动力的比例急遽下滑。不稳定无产阶级逐渐取代了上班族,造成自杀与各种社会病态的比例急遽增加。[4]
90年代末为什么中国、日本、韩国纷纷进行劳动市场的结构改革?相似的背景是全球资本主义,在后福特主义生产体制时代,弹性已经成为竞争力和经济成功的同义词。追求弹性劳动关系,将劳动再商品化(labour re-commodification)的过程中,劳动关系变得对市场供需更敏感,并且用价格(工资)来衡量,侵蚀劳动安全,这是全球不稳定无产阶级增长的主要直接原因。
《不稳定无产阶级》书里描述人们从长期雇佣到失去稳定身分后的状态:“日本上班族转变的例子可能很极端,但它让我们看见,长期聘雇关系会如何限制员工的心理发展,让人失去对自我的掌控,陷入职位不稳定的危机。因为他们没有独立维生的技能,也没有发展自己的特长。长期聘雇关系会让人失去技能。”
小三白提到自己不适应那种大规模用工的需求,所以也有半被迫失业的部分。什么是一个合格的工人?
事实上,当我再往前追溯历史时,我发现在工业化的早期,当时的乡下人也一样不愿意每天花费十几个小时被关在工厂里照看机器,他们拒绝服从由工头、时钟和机器设定的生活节奏。这种恶习被视为建立一个美丽新世界的最大障碍。意识到问题严重性的经济学家和布道者发起「工作伦理」改革运动。
「工作伦理」是早期被建构出来的,是一场关于控制和服从的战争。
真正的故事与与后来经济学家、历史学家认为的历史真相也恰恰相反。工厂体系的诞生事实上瓦解了工匠和他们的事业之间的亲密关系。 在过去,工人通过自己设定目标、自己控制进程获得工作的意义和动力,但现在,他们只能被动地完成由他人设置和控制的任务,工作对他们而言失去了意义。在这种转变之下,如何驱动工人运用自己的技能完成这些没有意义的任务,是现代化的开拓者面临的真正问题。[5]
在当下,工作变得唯市场为中心的计算,并且变得流动、不稳定,人如何处理与工作的关系?如何构建自己稳定的位置?《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给出一个答案是以工艺伦理(ethics of workmanship)取代劳动力市场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工作伦理。或许这也是上文讨论的「工作」和「做事儿」的区别?
索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早就指明,“工艺本能”(instinct of workmanship)有别于工作伦理这个现代发明,是人类的自然倾向。人是具有创造力的生物。如果认为标价牌是区分工作与非工作、努力与懒惰的标准,那是对人类本性的贬低。工艺伦理将恢复人类本能的尊严,恢复社会公认的意义。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形成且根深蒂固的工作伦理却否认了这种尊严和意义。[5]
References
[1] 黑5类:政治身份为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等“五类分子
[2] 《韩国工人:阶级形成的文化和政治》
[3] 王晓玲:韩国的“人口危机”与年轻人的“脱轨人生”
[4] 《不稳定无产阶级》
[5]《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
「工作的对谈」是由大憨撰写的一份对话笔记,一份身边人「工作状态」的田野手记。如果这些对话文本也让你共鸣,来给大憨回信。